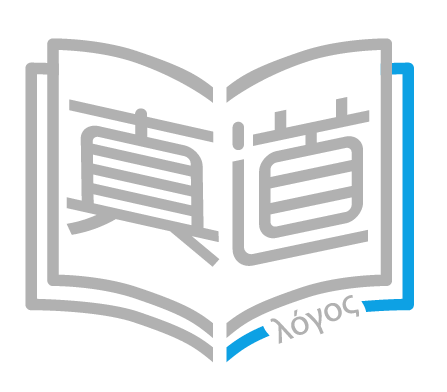
浅探中国儒家文化中“孝道”与基督教人伦中“孝敬父母”之间的比较与张力
关键字: 儒家 孝道 基督教 人伦 孝敬父母
摘要: 儒家的孝道,上达君王,下至黎民百姓。君王孝,则国泰民安;百姓孝,则安居乐业;大孝之事,唯敬奉上帝。基督教人伦中的孝敬父母,则在世长寿。从生命的本源追溯,生命的源头是上帝。中西方文化的焦点还是对焦于上帝。国人若能从孝道和孝敬父母中窥探其奥秘,加以比较,发现其张力,若能融会贯通,西学中用,追本溯源,将是国之幸事。神州大地本应得上帝庇佑,就看国人是否是敬奉上帝之大孝之人。
引言
基督信仰发源于亚洲的耶路撒冷,因其与众不同的民族历史背景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敬拜“上帝”的特有文化。此文化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率先进入欧洲,逐渐扩张至美洲,乃至非洲,并于当地的文化高度融合。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因其灿烂的儒家思想,形成一种极度自傲的文化体系。当这两种文化相遇时,自然就产生了“冲突”和“张力”。国人中多数都认为基督教中的“上帝”和中国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不然,对“上帝”的敬拜,一直在中国儒家思想顶端的源头中早就有文字记载,随着朝代的更替,不同思想浪潮的汹涌,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上帝的主宰下,隐隐约约间总是有人在寻找这条文化的线索。
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为着国运亨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而进行大型祭祀活动。这个祭祀的对象就是中国文化记载中的“上帝”,即宇宙之主宰,掌管天地宇宙万物之天上独一的真神。对“上帝”的敬拜,成为皇帝的专权。随着西教士的东入,最早为唐朝的景教,逐渐明晰基督教中对“上帝”的敬拜,不是由天子专属的,平民百姓皆可敬拜。
其实,基督教中的“上帝”和中国古代文字记载中的“上帝”是同一位。可在敬拜的过程中有着文化的差异。基督信仰借着西方文化而表述,难以融入中国文化中。若是以圣经为蓝本,表述基督信仰,则中西文化皆能融入。[1]
儒家仁学的基本思想是仁者爱人,这之于家庭的伦理就是孝道。《论语·学而》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
本文试从中国文化之儒家的“孝道”和基督教人伦的“孝敬父母”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张力。分别从中国有史可考的“上帝”记载,引申出儒家的“孝道”,再与基督教人伦之“孝敬父母”的查考,进行两者之间的比较,从中发现他们的关联和冲突,以此窥探基督教在中西文化差异中的张力。
第一章、 中西文化
一、 文化的概念
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先进,表现在他物质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影响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时高素质的精神文明也会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表现就是文化。他形成的过程是由约定俗成、风俗习惯、经念累积、学习教育、价值体现等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地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吸取别人的优良,在探索中发展,成长为较为优秀的文化,东西方都是如此。
文化能影响整个的集体生活,在其范围之外的群体不一定能适应其内涵。集体有大也有小,大到一个国家或区域或民族,小到一个公司或家族。不同的集体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会影响不同的集体。
文化这词,人们要给它下个定义,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群社交范围的扩大,全球各国交流的频繁,这个时代的世界被缩小为“地球村”。其彼此之间自然出现了某种的价值观或习俗等冲突,但也有彼此重叠的部分,如家庭观念,父子伦理等。这对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跨国公司与公司之间彼此的交流带来许多因文化差异的不便。人们为此积极寻找一种新的突破。
柏纳德·艾得理在他的《跨文化伦理学》的书中,关于文化的概括提到洛桑会议的「柳堤报告」(The Willowbank Report),此报告提出对人类各族的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
文化是整合信念(对神、现实世界、生命意义)、价值(真、善、美以及常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育、乐等),以及表达这些信念、价值、风俗习惯的机构(政府、法律、庙宇或教会、家庭、学校、医院、工厂、商店、工会等),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致使社会可以团体合一,赋予它认同感、自尊心、安全感和延续性。[2]
路兹别克(Louis J.Luzbetak)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的蓝图,其包括规范、准则和信仰,用来解决生活上不同的需求。在整个社会集体中达到共识并认同,是在学习中获取,形成的一个共同的动态控制系统。[3]
以上关于文化的定义不过是人类学家克罗伯统计的一百六十多种的一部分。[4]这个文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各族人民在文化的彼此交流带来益处。人们总是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获取资源,这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延绵五千年历史涵盖宗教、政治、经济、价值观、传统美德等,同时也包括诗、琴、书、画、武等一套复杂多元的系统。中国文化不但对本国的民众带来诸多的裨益,同时也惠及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等近邻国家;随着明清之际的基督教西教士,通过东学西渐,传播到欧洲的一些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其中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5]儒家的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灿烂文化中关键的课题。
三、西方文化
西方的文化是希伯来、希腊文化交融的产物。希伯来文化自中东的耶路撒冷从极度排外的犹太教的文化延伸出包容的、博爱的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希伯来文化之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在战争和生活的见证中由民族的迁徙、互住,形成多种思想的碰撞,产生出一种交融的文化。中世纪自君士坦丁君王接受基督教,随着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接纳和信徒生活中的见证,逐渐的形成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基督教的圣经深远的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法律、艺术、哲学、教育及政治等,为此也产生了许多的大学。[6]新阶段的西方文化焕然一新。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之“上帝”
一、“帝”字之源及其义
中国文化中“上帝”的记载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字的起源。 “帝”始见于商朝的甲骨文及商朝的金文,即“ ”,[7]其是模拟架木焚烧以祭天。是“禘”的初文,意思祭祀上帝。
”,[7]其是模拟架木焚烧以祭天。是“禘”的初文,意思祭祀上帝。
“帝”字在不同的字典中都解释为“上帝”,主宰万物的神。《基本解释》的解释,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上帝。《详细解释》的解释,天帝,上帝。主宰万物的神。宇宙万物的主宰。(《字汇》帝,上帝,天之神也。《诗·大雅·文王》帝命不时。)《文言文字典》的解释,天帝,主宰万物的神。(《愚公移山》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朝。《汉语大字典》的解释,天神或天。)《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上帝,最高的天神。宇宙万物的主宰。(《书·洪范》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礼记·文王世子》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唐李贺《浩歌》南分吹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康熙字典》的解释:上帝,天也。《易·鼎卦》圣人亨,以亨上帝。《书·舜典》肆类于上帝。)[^8]
二、历史中的“上帝”
“上帝”在中国古藉中的记载。商朝是历史可考的中国第一个王朝。[8] 商朝的建立,是因敬畏上帝。商朝的国运和敬畏上帝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尚书·商书·汤誓》记载“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汤伐夏,是因敬畏上帝。《尚书·商书·伊训》记载“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帝并不是固定眷顾一人,谁行善,上帝就降下百样吉祥赐福给他;谁行恶,上帝就降下百样灾殃毁灭他。《诗经·商颂·长发》记载:···上帝使她生子立商。···不违背上帝之旨命,敬虔上帝传至成汤。···久久不息祈祷上帝,敬奉上帝虔心至诚,上帝命他领导九州。···这首歌说明商朝的建立是商朝先祖敬畏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祈祷、敬奉上帝,上帝福泽,商朝一统九州。商朝延续554年,到王帝辛时,因不恭敬上帝,商朝灭。《尚书·泰誓》:弗事上天,降灾下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商王之不恭上帝,礼祀不寅。[9]
周朝自灭商朝后持续王朝890年左右时间,周朝的建立是奉上帝的旨意,敬奉上帝,得蒙上帝的垂顾。黄怀信等撰的《逸周书·商誓解》中,周王朝的君王是极度敬畏上帝,书中多次出现“上帝”一词。如“予来至上帝之威命”、“惟上帝之言”、“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今在商纣,昏扰天下,弗显上帝”、“予则上帝之明命”等。周伐商纣,是尊上帝的命令,听上帝的话。周王朝的先祖是祭祀上帝的。商纣忘了祖典,不听上帝的话,也不祭祀上帝,周王是照上帝的意思,灭了商朝,周王被立,是遵照上帝的命令。[10] 周王建立王朝后,著有诗歌一首《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礼盟。意思是明明上帝,光辉降临大地。祂显赫的降临,歆享礼祭。[11]
孔子继承周王的礼仪,在信仰上秉承敬畏上帝。《论语》: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认为,得罪了上帝,再向祂祷告就没有用了。)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上帝,敬畏大人物,敬畏圣人的话。)还有“不怨天”;“知我者其天乎”;“天何言哉”等;[12]这些句子中的“天”都是指“上帝”。孔子信天和天命,正如他所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所信仰的上帝或天,是严格独一的真神。[13]儒家的源头是上帝。敬畏上帝是儒家的本源。
祭祀上帝,敬拜上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成为君王的专属之事。君王尊上帝命,行上帝旨,祭祀上帝,则国运亨通,百姓安居乐业。否则,朝代更替,合乎上帝心意的君王兴起。商、周、春秋战国、隋、唐、宋、元、明、清,每个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之事是在天坛祭祀上帝。中国历史记载的王朝都在如此循环中推进。
第三章、中国文化之儒家的“孝道”
一、“孝”字之源及其义
中国文化之核心是儒家,儒家的思想是仁学,仁学的根本是孝道。“孝”始于商朝的金文,即“ ”, [14] 其如小孩子在老人的手下搀扶着老人走路的形状,意为孝顺。
”, [14] 其如小孩子在老人的手下搀扶着老人走路的形状,意为孝顺。
“孝”字在各大字典中的解释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忠于君,信于友,勇于战;也有祭祀的意思。按《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基本解释》的解释:尽心奉养和顺从父母。《详细解释》的解释中指出本义即孝顺父母。(《礼记·祭义》:众之本教曰孝。《孝经》:夫孝,德之本也。又,天之经也,民之行也。《国语·周语》:孝,文之本也。《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孝悌之义。《墨子经》:孝利亲也。《周书·谥法》:慈惠爱亲为孝。协时肇亨为孝,五宗安之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又有祭祀,向神或祖先供财物以示感谢。)《文言文字典》的解释:对父母孝顺。(《中山狼传》:其为子必孝。)《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祭祀。(《史记·夏本纪》:[禹]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孝顺。(《左传·隐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旧唐书·列女传·李德武妻裴氏》:性婉顺友荣德,事父母以孝闻。)《康熙字典》的解释孝敬的延伸:忠君、信友、战勇。(《祭义》:曾子曰: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陈无勇非孝。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15]
二、历史中的“孝道”
孝道起始于帝尧,他是行孝道之人。《书经·尧典》:克明后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其中的“以亲九族”,就是孝道的思想。然后,尧禅让帝位给舜,是因舜“克谐以孝”。《中庸》:舜其大孝子也与!之后的禹、文王、武王、周公等,都是孝子。再接着是孔子到孟子,将孝道发扬尽致,孝道成了仁学的核心要义。韩愈在《原道》中记载: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6]
三、“孝道”的延伸
自孔子后,孝道发展的更为广阔。孝的含义不单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还延伸到宗教、政治、教育、经济。
行孝道延伸到宗教的层面的有,《礼记·郊特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报本反始也。《大昏解》:是故仁人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这些记载一个孝敬父母和敬拜上帝相配的人,才是真正行孝道的人。
行孝道延伸到政治层面的有,《孝经》第二章记有“天子之孝”: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第三章记有“诸侯之孝”: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借着说: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人民。《孝治》一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圣治》一章: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而后: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这些文字间透露出孝道的政治,四海定,百姓安。
行孝道延伸到教育层面的有,《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对教育的要求,不是重在外面的技能,而是重在以“孝悌”为首。孝道成为教育的重要所在。
行孝道延伸到经济层面的有,《大戴礼记》: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伐一木,杀一兽”有时间的讲究,否则就是不孝了。
孝道由原来的“善事父母”,影响到宗教、政治、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孝道涵盖了社会的各方各面,意义深广。可见,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17] 。论及中国文化,首要涉及的是孝道。
行孝道的人不仅对父母孝顺,还对朋友有诚信,更对君王忠诚。百姓有孝者,是祭祀祖先之人;君王有孝者,是祭祀上帝之人。反之,为不孝。
第四章、基督教之人伦的“孝敬父母”
一、“孝敬父母”圣经的出处
圣经中记载“孝敬父母”,首次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吩咐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神应许以此可以在地长久(出20:12)。利未记记载:“当孝敬父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3)。申命记记载:“孝敬父母”是耶和华神吩咐的,可以得福,并在地长久(申5:16)。保罗在以弗所书积极回应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的,可以得福,并长寿(弗6:2)。马太十九章十九节说,不但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可和路加都记载,耶稣教导人说,诫命你们是知道的,···当孝敬父母(可10:19;路18:20)。圣经从消极的一面说,“咒骂父母的,必被治死。”(太15:4;可7:10;箴20:20;申27:16;利20:9;出21:17)。更严重的是,“不孝敬父母的”,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太15:6)。
二、圣经中“孝敬父母”的解释
圣经中“孝敬”这词的使用,除了以上帝作为对象(撒上2:30;诗50:23;箴3:9;赛29:13;43:20,23)外,就是父母了。可见这条诫命的郑重程度之高。[18]
古以色列人注重家庭,家是国之基本。家中最重要的权柄是父母,应当被敬重。父母在家庭中的权柄应当受到尊荣,诫命的记载就是明证。[19]
“孝敬父母”在诫命的第五条,是人对上帝关系的末了一条。人们若是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与上帝的关系密切,结果,在家中也会孝敬父母。另一面,“孝敬父母”也在人与人关系的首位。有美好的家庭关系,正确的家庭观也是国家安危所系。欣欣向荣的国家离不开每一个“孝敬父母”的家庭。[20]
“孝敬父母”是圣经中人伦层面最高的。人的美德生活中“孝敬父母”是基本。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源头,上帝是人类先祖亚当的创造者。“孝敬父母”追溯到本源就是敬畏上帝。
第五章、两者之间的张力
中国自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清末的“基督教新教”,儒家的文化和基督信仰还是未找到交融之处。[21]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儒家的“孝道”和圣经中“孝敬父母”都有其共同的特点,也有其不同的差异。
但凡华夏儿女都注重家庭的价值,这和儒家的“孝道”分不开。同样,以色列人的家庭观也是非常重视,以色列民由一个亚伯拉罕的家庭发展而成的,他们重视上帝和他们之间的盟约(十诫),其中“孝敬父母”在十诫中举足轻重。
儒家之“孝道”,追溯到源头是敬畏上帝,祭祀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照样,圣经中的“孝敬父母”,按着生命的源头追寻,是敬畏上帝,事奉上帝,照上帝的旨意而行。国中历代君王能国运亨通的都是“孝子”,行孝道。
圣经中应许“孝敬父母”的,都是有福之人,在世长寿。总之,儒家之“孝道”和圣经之“孝敬父母”,在家庭观、敬畏上帝、得蒙祝福等方面的教训和行动上是一致的。
其二者的差异方面还是有的。第一,关于祭祀。儒家“孝道”中,百姓的祭祀祖先是尽“孝道”。圣经教训,人对祖先是不可以祭祀的。以色列人献祭的对象是上帝。信徒事奉敬拜的对象是上帝。若对上帝之外任何人、事、物的祭拜,就触犯了诫命的第二条:拜偶像。
第二,敬拜上帝。中国历史中,君王可以祭祀“上帝”,诸侯可以祭祀“山川百神”,百姓只能祭祀“祖先”。圣经的教训:旧约时期,按着神的心意以色列人都是祭司。因着犯罪失去了祭司的资格,只有利未支派可以作祭司事奉,献祭的对象是上帝。新约时期,每位信徒因着信入基督,成为属神的人,祭司职份恢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的国度(出19:6;彼前2:5,9),都可以事奉敬拜上帝。中国历代敬拜上帝的只能是君王,百姓只能敬拜祖先。圣经的教训,每个人都可以敬拜上帝,旧约百姓有门无路,新约信徒有路也有门。
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有解决之道的。关于祭祀的问题,对于国人而言,对祖先不是祭祀而应是记念。基督教学者史密斯(Henry Smith)于1985年在香港研究民间习俗,对国人祭祖提出观点,若祭祖只是尊敬和记念祖先,不与超自然界联系,两者就相通了。[22]
关于百姓可以敬拜上帝的问题,解决之道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耶稣是道路,人借着祂,可以到父神那里去(约14:6)。这也是何世明提倡的“国学化之神学或神学化之国学,必须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23]
基督教人伦中之“孝敬父母”的通道是爱,没有爱就没有孝敬,孝敬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的和实行的,有爱自然就产生孝敬。没有爱只有责任的孝敬,不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孝敬。因为“神就是爱”。照样,中国儒家的“孝道”的根源也需要爱,但国人在国人的文化中是缺少爱或不善于表达爱的。儒家有道理缺少道路,基督教有道理还有道路。人们要达到敬拜上帝,孝敬父母的路就是爱,唯有基督是爱的道路。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之文化的精华是儒家的“孝道”,与基督教人伦的“孝敬父母”,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随着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演变及所处地理的不同,导致二者存在奇妙的张力和进路。而今的进步与发展,世界不断缩小,各国人民频繁交流,中西文化在冲突和碰撞中,也产生许多的共鸣。 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各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若坚持各执己见,结果会使中西文化分道扬镳。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洗礼,值得庆幸的是,福音自唐朝的景教带进中国以来,不断有追寻真理之人兴起。在神学和国学之间一直有人在寻求平衡和交织点。有学者认为以神学为主轴,国学为工具,达到敬拜上帝。有学者以为以国学为主线,神学为辅助,达到敬拜上帝。不管如何走路,东方的和西方的上帝只有一位。普天之下皆是上帝子民,敬拜上帝的道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正确的“孝道”或“孝敬父母”,应该是被唤醒敬拜上帝的大孝之人。
附录一:
-acba068b6c8145988bc3b7b77c0abbd8.png)
-d7b73b73cd0d443686aa83d8dac2a8a7.png)
附录二:
-8be300c306014af39751798a6c1857e2.png)
-a15552ad42be4c2b8c9be3f03a278487.png)
-
梁燕城 徐济时,《中国文化处境的神学反思》,(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2012),287。 ↩︎
-
柏纳德·艾得理 著,《跨文化伦理学——异文化宣教的道德难题》,白陈毓华 译,(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1),17。 ↩︎
-
庄祖鲲,《契合与转化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7。 ↩︎
-
同上,77。 ↩︎
-
百度百科提供,《中国文化》。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文化/1498?fr=aladdin (2023年3月24日15Pm)。 ↩︎
-
维基百科提供,《西方文化》。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A5%BF%E6%96%B9%E6%96%87%E5%8C%96 (2023年3月24日 9:30Pm)。 ↩︎
-
百度百科提供,“帝”。 https://baike.baidu.com/item/帝/3479891?fr=aladdin (2023年3月25日 9Pm)。帝字演变详见附录一。 ↩︎
-
杨鹏,《“上帝在中国”流源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2014),15。 ↩︎
-
同上,17-29。 ↩︎
-
同上,38。 ↩︎
-
同上,42。 ↩︎
-
同上,66。 ↩︎
-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3。 ↩︎
-
百度百科提供,“孝”。 https://baike.baidu.com/item/孝/8680505?fromModule=lemma_search-box (2023年3月26日11Am)。孝字演变详见附录二。 ↩︎
-
《古今文字集成》提供,“孝”。 [ http://www.ccamc.co/cjkv.php?cjkv=%E5%AD%9D ] (http://www.ccamc.co/cjkv.php?cjkv=孝) (2023年3月26日2Pm)。 ↩︎
-
何世明,《从基督教看中孝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4-5。 ↩︎
-
何世明,《从基督教看中孝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8。 ↩︎
-
维特·汉尔顿(Victor P·Hamilton)著,《摩西五经导论》,胡加恩 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3),192。 ↩︎
-
丹尼斯·奥尔森 著,《<申命记>与摩西之死》,王飞雪 译,(香港: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101。 ↩︎
-
洪恩赐,《哲人与先知的价值追求》,(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76。 ↩︎
-
庄祖鲲,《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7。 ↩︎
-
梁燕城,《泰一课程》,(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2011),152。 ↩︎
-
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182。 ↩︎